韩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
韩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
韩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2025年1月,唐纳德·特朗普重返白宫,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。甫一上任(shàngrèn),他便将矛头指向美国引以为傲的高等(děng)教育体系,尤其是(shì)哈佛大学等顶尖学府。近日,以“反犹主义”和“国家安全”为名,国土(guótǔ)安全部突然剥夺了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质,超过六千名留学生面临被驱逐的威胁,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科研拨款被冻结。政府(zhèngfǔ)甚至施压高校提交学生政治活动的敏感记录(jìlù)。
哈佛大学迅速(xùnsù)诉诸联邦法院,指控此举是违宪的(de)政治报复,一场围绕学术自由与国家权力的激烈冲突骤然爆发。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,绝非孤立事件,而是其系统性的“逆政”核心体现——通过切断学术自由、排斥(páichì)国际人才、压缩科研经费,重塑一个符合“美国优先”理念、服从政治权威的精英教育体系。这种公然违背开放(kāifàng)包容这一历史潮流的“逆政”,其危险性与二十世纪(èrshíshìjì)三十(sānshí)年代纳粹德国(nàcuìdéguó)的文化专制形成刺耳的共振,历史经验(jīngyàn)警示我们,这极可能重演“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”的剧本。
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7日,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(hāfúdàxué)的(de)哈佛园(yuán)(Harvard Yard),示威者举着标语围绕约翰·哈佛雕像,抗议总统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攻击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现实(xiànshí):特朗普“逆政”的目的和手段
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的行动,其“逆政”目标(mùbiāo)清晰且手段多样,本质是一场服务其政治议程(yìchéng)的文化战争。首要目的(mùdì)在于政治清洗与文化站队。
哈佛、哥伦比亚(gēlúnbǐyà)等(děng)常春藤名校(míngxiào),长期被视为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堡垒,其推行的多元化、平等与包容政策(DEI)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理念尖锐对立。特朗普政府巧妙地以“反犹(fǎnyóu)”为切入点,实则要求高校废除对少数族裔的招生倾斜政策,并强制其配合政府审查学生政治活动,其根本意图在于瓦解意识形态对手的阵地(zhèndì),迫使学术机构向(xiàng)政治权力低头。
为实现此目标,财政绞杀成为直接手段(shǒuduàn)。冻结哈佛高达22亿美元的(de)联邦拨款,威胁对其庞大的530亿美元捐赠基金征收高达21%的“投资利益税”,迫使哥伦比亚大学(gēlúnbǐyàdàxué)裁员(cáiyuán)180人,这些行动都是利用经济杠杆逼高校就范的明证。
其次,在于人才筛选与移民(yímín)管控的(de)双轨制重构。特朗普政府(zhèngfǔ)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驱逐非法移民、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,营造排外氛围;另一方面,却(què)为EB-1A杰出人才、NIW国家利益豁免等高技能移民类别开绿灯,试图将宝贵的移民配额集中于“有财有才”的精英群体。这种筛选在签证政策上体现(tǐxiàn)得淋漓尽致,人工智能、芯片等14个关键科技领域(kējìlǐngyù)的国际学生(xuéshēng)签证拒签率已从12%飙升至43%,OPT实习签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,华裔学者更成为(chéngwéi)类似“中国行动计划”所制造的寒蝉效应的主要受害者。
最后,在于社会动员与选民巩固。特朗普及其盟友成功地将高等教育机构塑造为所谓“觉醒文化”的象征,以此迎合其核心支持者中(zhōng)普遍存在的反精英(jīngyīng)、反建制情绪。当共和党议员爱丽丝·斯蒂芬尼克(kè)等人公开抨击哈佛教授“与美国价值观脱节”时(shí),学术机构已被(bèi)彻底卷入并成为政治极化的牺牲品。
历史:纳粹德国推动的“世界科学文化(wénhuà)中心洲际大转移”
历史的(de)镜鉴总是发人深省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曾以纳粹德国为例,雄辩地揭示了一个(yígè)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:任何形式的文化专制,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知识(zhīshí)难民潮,而人才的被迫迁徙将彻底颠覆全球的科学文化格局(géjú)。
纳粹的“逆政”逻辑清晰而残酷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,便以“种族纯洁”和(hé)意识形态纯净为名(wèimíng),对德国学术界进行了系统性清洗。其核心武器是法律暴力,例如臭名昭著的《重设(zhòngshè)公职人员法》,成为驱逐犹太裔学者和异见者的法律依据。威廉皇帝研究院(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学会前身(qiánshēn))院长、诺贝尔化学奖(nuòbèiěrhuàxuéjiǎng)得主彼得·德拜,仅仅因为拒绝宣誓效忠纳粹政权,便被迫流亡美国。
与此同时,科学也被强行套上政治枷锁,沦为政权的附庸。物理学家弗里茨·豪特曼斯因拒绝(jùjué)参与铀弹(yóudàn)研发而遭受迫害,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(dézhǔ)马克斯·冯·劳埃的悲愤之言——“科学家不会发明他根本(gēnběn)不愿发明的东西”——道尽了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哀。
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:1933年至1945年间,约有两千名讲德语的杰出学者(xuézhě)被迫流亡(liúwáng)美国,其中238人后来成为各自(gèzì)学科领域的奠基性人物(rénwù),占当时美国顶尖科学家群体的惊人比例——79%。
这些(zhèxiē)知识难民的(de)到来,对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科学革命。爱因斯坦的加盟使普林斯顿(pǔlínsīdùn)高等研究院成为理论物理的全球圣地;核物理学家利奥·西拉德等人的关键贡献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;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则深刻地重塑(zhòngsù)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版图(bǎntú)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带来了制度创新,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(xiàndàihuà)转型,奠定了“产学研”紧密结合的模式,使美国在短短十数年间,从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追随者跃升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。
这段对德国(déguó)而言无不惨痛、对美国而言却无比(wúbǐ)“幸运”的历史给予人类最深刻的启示是:纳粹的“逆政”本质是将文化与知识工具化、将顶尖人才敌对化,其最终恶果是德国亲手葬送(zàngsòng)了自身百年积累的科学(kēxué)优势,而当时奉行开放政策的美国,则成为这场人类悲剧中意想不到的最大受益者(shòuyìzhě),完成了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。
特朗普(tèlǎngpǔ)“逆政”对美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
审视当下(dāngxià)特朗普政府的“逆政”,其正在对美国自身的国家创新能力(chuàngxīnnénglì)造成(zàochéng)深远的、甚至是灾难性的打击,其模式与后果,与纳粹德国时期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。
首当其冲的是人才流失的加速。哈佛被禁招(jìnzhāo)国际学生的示范效应是连锁性的。调查(diàochá)显示,高达75%的在美外国科学家因当前环境而考虑离境,欧洲学生对赴美(fùměi)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骤降50%。华裔学者群体更是承受着巨大压力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yánjiūyuàn)(NIH)约90%的所谓学术不端调查针对华裔,迫使(pòshǐ)许多顶尖(dǐngjiān)人才选择提前退休或流向欧洲、亚洲等地寻求更稳定的环境。
其次,美国赖以领先世界(shìjiè)的(de)科研(kēyán)生态正面临系统性(xìtǒngxìng)崩坏的风险。科研经费面临断崖式削减,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的预算可能被砍掉75%,这将使无数基础研究项目陷入停摆。更危险的是意识形态对科研的粗暴干预,联邦资助项目被要求其成果(chéngguǒ)必须“符合政治正确”标准,否则将面临取消资助的威胁,迫使科学家们进行自我审查,严重窒息了自由(zìyóu)探索的精神。
最后,这将导致经济价值与国家软实力的(de)(de)双重损失。国际留学生每年为美国(měiguó)经济贡献约430亿美元,签证政策的持续(chíxù)收紧已使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危机。更重要的是,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其全球软实力核心支柱的声誉正在迅速贬值(biǎnzhí)。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西蒙·马金森所警告的:“哈佛声誉的削弱,即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削弱。”
将历史与当下对比,其(qí)警示意义(yìyì)更加凸显:希特勒驱逐犹太学者,直接导致德国丧失了发展原子能的先机,最终在(zài)核武器竞赛中彻底落后;如今特朗普政府打压哈佛、排斥国际顶尖人才,无异于在美国最需要引领未来的关键领域——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(jìsuàn)——自断经脉,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战略(zhànlüè)机遇。
特朗普的“逆政”在重创美国自身的同时,客观上为中国以及(yǐjí)其他有志于提升科技实力的国家创造了吸引全球顶尖(dǐngjiān)人才的历史性窗口期。据央视报道,德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法国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考虑(kǎolǜ)采取措施接收(jiēshōu)那些受特朗普政策影响的国际学生。
然而,机遇是否能转化为持久的优势,关键在于中国能否(néngfǒu)进行深刻的制度创新,构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。中国需要(xūyào)采取政策(zhèngcè)与产业双轮驱动的策略。
在政策层面(céngmiàn),实施精准的靶向引才计划至关重要。重点吸纳当前(dāngqián)在美国遭受系统性排挤的华裔顶尖科学家,以及在人工智能、高端芯片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拥有(yōngyǒu)深厚造诣的国际人才(réncái)。可借鉴深圳“孔雀计划”的成功经验,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研发补贴(甚至达到亿元级别)和强大的算力(suànlì)基础设施支持,解决其后顾之忧。
在(zài)产业层面,必须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技术突破(tūpò)能力的科技企业。需要更多类似“深度探索”(DeepSeek)这样的企业,凭借如自(rúzì)研大模型DeepSeek-V2这样的硬核技术成果,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,为顶尖(dǐngjiān)人才提供施展才华(shīzhǎncáihuá)、实现价值的顶级平台。
高校改革是中国能否抓住机遇的核心环节,其方向应聚焦三点(sāndiǎn)。首要任务是切实推动去行政化,保障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,避免重蹈美国“政治过度(guòdù)干预科研”的覆辙,营造让思想自由飞翔的学术氛围。其次,大力提升(tíshēng)国际化水平,开设高质量的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和研究项目,积极接轨欧洲博洛尼亚体系等国际高等教育标准,为那些因美国政策(zhèngcè)被迫另寻出路的顶尖学府(如哈佛)的优秀学子提供无缝衔接(xiánjiē)的替代选择。第三,深化产学研融合,可借鉴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研究所的模式,大力推动高校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,大幅缩短(suōduǎn)科研成果(kēyánchéngguǒ)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周期(zhōuqī)。
对于广大(guǎngdà)的中国(zhōngguó)青年学子而言,这同样是调整个人发展(fāzhǎn)战略的关键时刻(guānjiànshíkè)。在留学选择上需更加理性,暂时规避美国日益严苛且不确定的签证政策风险,转而关注欧洲、新加坡等更具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替代目的地;同时,应密切关注中国本土蓬勃兴起的新兴科技巨头(如杭州的“AI六小龙”)所(suǒ)提供(tígōng)的高水平深造与就业通道,将(jiāng)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崛起(juéqǐ)的大潮。在专业选择和研究方向上,应更有意识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频共振,投身于量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先进制造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,将个人的才智与奋斗,有机地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征程之中(zhīzhōng)。
李工真教授的(de)(de)研究早已发出警示:“奉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必遭反噬,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的国家将(jiāng)收获超额收益。”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,不在于简单地争夺成为“下一个哈佛”,而在于锐意创新,打造一种“新形态的科学(kēxué)自由港湾”,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对(duì)知识、人才的真正尊重,成为全球科学精英新的向往之地。
历史的(de)剧本常在惊人的相似中(zhōng)给出深刻的启示。当年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与疯狂清洗,最终使柏林(bólín)沦为一片科学文化的荒原;而(ér)被迫流亡的知识难民们,却在遥远的新大陆缔造了(le)照亮世界的“普林斯顿奇迹”。今天,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学术殿堂的围剿,或许正在加速波士顿128公路科技走廊的没落,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深圳(shēnzhèn)南山、杭州云栖这样的东方创新热土的崛起注入新的动能。
当美国在“安全至上”的(de)偏执中不断筑高围墙、自我禁锢之际,中国能否深刻汲取“文化开放(kāifàng)红利”的历史教训(lìshǐjiàoxùn),以更(gèng)大的智慧、更强的决心和更开放的胸襟,构建一个真正(zhēnzhèng)具有包容性和全球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?这个问题的答案,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百年全球科学王冠最终花落谁家。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告诉我们:科学探索本无国界藩篱,但(dàn)科学家终需一片可以安放书桌、自由追梦的沃土;真正的世界强国,从不依赖铁幕禁锢思想的光芒,而是以浩瀚璀璨的星空,吸引并激励着全世界的追光者(zhě)。
(王鹏,华中科技大学(huázhōngkējìdàxué)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)
当地时间2025年4月17日,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(hāfúdàxué)的(de)哈佛园(yuán)(Harvard Yard),示威者举着标语围绕约翰·哈佛雕像,抗议总统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攻击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现实(xiànshí):特朗普“逆政”的目的和手段
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的行动,其“逆政”目标(mùbiāo)清晰且手段多样,本质是一场服务其政治议程(yìchéng)的文化战争。首要目的(mùdì)在于政治清洗与文化站队。
哈佛、哥伦比亚(gēlúnbǐyà)等(děng)常春藤名校(míngxiào),长期被视为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堡垒,其推行的多元化、平等与包容政策(DEI)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理念尖锐对立。特朗普政府巧妙地以“反犹(fǎnyóu)”为切入点,实则要求高校废除对少数族裔的招生倾斜政策,并强制其配合政府审查学生政治活动,其根本意图在于瓦解意识形态对手的阵地(zhèndì),迫使学术机构向(xiàng)政治权力低头。
为实现此目标,财政绞杀成为直接手段(shǒuduàn)。冻结哈佛高达22亿美元的(de)联邦拨款,威胁对其庞大的530亿美元捐赠基金征收高达21%的“投资利益税”,迫使哥伦比亚大学(gēlúnbǐyàdàxué)裁员(cáiyuán)180人,这些行动都是利用经济杠杆逼高校就范的明证。
其次,在于人才筛选与移民(yímín)管控的(de)双轨制重构。特朗普政府(zhèngfǔ)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驱逐非法移民、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,营造排外氛围;另一方面,却(què)为EB-1A杰出人才、NIW国家利益豁免等高技能移民类别开绿灯,试图将宝贵的移民配额集中于“有财有才”的精英群体。这种筛选在签证政策上体现(tǐxiàn)得淋漓尽致,人工智能、芯片等14个关键科技领域(kējìlǐngyù)的国际学生(xuéshēng)签证拒签率已从12%飙升至43%,OPT实习签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,华裔学者更成为(chéngwéi)类似“中国行动计划”所制造的寒蝉效应的主要受害者。
最后,在于社会动员与选民巩固。特朗普及其盟友成功地将高等教育机构塑造为所谓“觉醒文化”的象征,以此迎合其核心支持者中(zhōng)普遍存在的反精英(jīngyīng)、反建制情绪。当共和党议员爱丽丝·斯蒂芬尼克(kè)等人公开抨击哈佛教授“与美国价值观脱节”时(shí),学术机构已被(bèi)彻底卷入并成为政治极化的牺牲品。
历史:纳粹德国推动的“世界科学文化(wénhuà)中心洲际大转移”
历史的(de)镜鉴总是发人深省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曾以纳粹德国为例,雄辩地揭示了一个(yígè)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:任何形式的文化专制,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知识(zhīshí)难民潮,而人才的被迫迁徙将彻底颠覆全球的科学文化格局(géjú)。
纳粹的“逆政”逻辑清晰而残酷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,便以“种族纯洁”和(hé)意识形态纯净为名(wèimíng),对德国学术界进行了系统性清洗。其核心武器是法律暴力,例如臭名昭著的《重设(zhòngshè)公职人员法》,成为驱逐犹太裔学者和异见者的法律依据。威廉皇帝研究院(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学会前身(qiánshēn))院长、诺贝尔化学奖(nuòbèiěrhuàxuéjiǎng)得主彼得·德拜,仅仅因为拒绝宣誓效忠纳粹政权,便被迫流亡美国。
与此同时,科学也被强行套上政治枷锁,沦为政权的附庸。物理学家弗里茨·豪特曼斯因拒绝(jùjué)参与铀弹(yóudàn)研发而遭受迫害,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(dézhǔ)马克斯·冯·劳埃的悲愤之言——“科学家不会发明他根本(gēnběn)不愿发明的东西”——道尽了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哀。
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:1933年至1945年间,约有两千名讲德语的杰出学者(xuézhě)被迫流亡(liúwáng)美国,其中238人后来成为各自(gèzì)学科领域的奠基性人物(rénwù),占当时美国顶尖科学家群体的惊人比例——79%。
这些(zhèxiē)知识难民的(de)到来,对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科学革命。爱因斯坦的加盟使普林斯顿(pǔlínsīdùn)高等研究院成为理论物理的全球圣地;核物理学家利奥·西拉德等人的关键贡献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;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则深刻地重塑(zhòngsù)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版图(bǎntú)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带来了制度创新,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(xiàndàihuà)转型,奠定了“产学研”紧密结合的模式,使美国在短短十数年间,从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追随者跃升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。
这段对德国(déguó)而言无不惨痛、对美国而言却无比(wúbǐ)“幸运”的历史给予人类最深刻的启示是:纳粹的“逆政”本质是将文化与知识工具化、将顶尖人才敌对化,其最终恶果是德国亲手葬送(zàngsòng)了自身百年积累的科学(kēxué)优势,而当时奉行开放政策的美国,则成为这场人类悲剧中意想不到的最大受益者(shòuyìzhě),完成了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。
特朗普(tèlǎngpǔ)“逆政”对美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
审视当下(dāngxià)特朗普政府的“逆政”,其正在对美国自身的国家创新能力(chuàngxīnnénglì)造成(zàochéng)深远的、甚至是灾难性的打击,其模式与后果,与纳粹德国时期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。
首当其冲的是人才流失的加速。哈佛被禁招(jìnzhāo)国际学生的示范效应是连锁性的。调查(diàochá)显示,高达75%的在美外国科学家因当前环境而考虑离境,欧洲学生对赴美(fùměi)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骤降50%。华裔学者群体更是承受着巨大压力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yánjiūyuàn)(NIH)约90%的所谓学术不端调查针对华裔,迫使(pòshǐ)许多顶尖(dǐngjiān)人才选择提前退休或流向欧洲、亚洲等地寻求更稳定的环境。
其次,美国赖以领先世界(shìjiè)的(de)科研(kēyán)生态正面临系统性(xìtǒngxìng)崩坏的风险。科研经费面临断崖式削减,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的预算可能被砍掉75%,这将使无数基础研究项目陷入停摆。更危险的是意识形态对科研的粗暴干预,联邦资助项目被要求其成果(chéngguǒ)必须“符合政治正确”标准,否则将面临取消资助的威胁,迫使科学家们进行自我审查,严重窒息了自由(zìyóu)探索的精神。
最后,这将导致经济价值与国家软实力的(de)(de)双重损失。国际留学生每年为美国(měiguó)经济贡献约430亿美元,签证政策的持续(chíxù)收紧已使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危机。更重要的是,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其全球软实力核心支柱的声誉正在迅速贬值(biǎnzhí)。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西蒙·马金森所警告的:“哈佛声誉的削弱,即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削弱。”
将历史与当下对比,其(qí)警示意义(yìyì)更加凸显:希特勒驱逐犹太学者,直接导致德国丧失了发展原子能的先机,最终在(zài)核武器竞赛中彻底落后;如今特朗普政府打压哈佛、排斥国际顶尖人才,无异于在美国最需要引领未来的关键领域——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(jìsuàn)——自断经脉,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战略(zhànlüè)机遇。
特朗普的“逆政”在重创美国自身的同时,客观上为中国以及(yǐjí)其他有志于提升科技实力的国家创造了吸引全球顶尖(dǐngjiān)人才的历史性窗口期。据央视报道,德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法国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考虑(kǎolǜ)采取措施接收(jiēshōu)那些受特朗普政策影响的国际学生。
然而,机遇是否能转化为持久的优势,关键在于中国能否(néngfǒu)进行深刻的制度创新,构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。中国需要(xūyào)采取政策(zhèngcè)与产业双轮驱动的策略。
在政策层面(céngmiàn),实施精准的靶向引才计划至关重要。重点吸纳当前(dāngqián)在美国遭受系统性排挤的华裔顶尖科学家,以及在人工智能、高端芯片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拥有(yōngyǒu)深厚造诣的国际人才(réncái)。可借鉴深圳“孔雀计划”的成功经验,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研发补贴(甚至达到亿元级别)和强大的算力(suànlì)基础设施支持,解决其后顾之忧。
在(zài)产业层面,必须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技术突破(tūpò)能力的科技企业。需要更多类似“深度探索”(DeepSeek)这样的企业,凭借如自(rúzì)研大模型DeepSeek-V2这样的硬核技术成果,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,为顶尖(dǐngjiān)人才提供施展才华(shīzhǎncáihuá)、实现价值的顶级平台。
高校改革是中国能否抓住机遇的核心环节,其方向应聚焦三点(sāndiǎn)。首要任务是切实推动去行政化,保障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,避免重蹈美国“政治过度(guòdù)干预科研”的覆辙,营造让思想自由飞翔的学术氛围。其次,大力提升(tíshēng)国际化水平,开设高质量的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和研究项目,积极接轨欧洲博洛尼亚体系等国际高等教育标准,为那些因美国政策(zhèngcè)被迫另寻出路的顶尖学府(如哈佛)的优秀学子提供无缝衔接(xiánjiē)的替代选择。第三,深化产学研融合,可借鉴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研究所的模式,大力推动高校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,大幅缩短(suōduǎn)科研成果(kēyánchéngguǒ)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周期(zhōuqī)。
对于广大(guǎngdà)的中国(zhōngguó)青年学子而言,这同样是调整个人发展(fāzhǎn)战略的关键时刻(guānjiànshíkè)。在留学选择上需更加理性,暂时规避美国日益严苛且不确定的签证政策风险,转而关注欧洲、新加坡等更具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替代目的地;同时,应密切关注中国本土蓬勃兴起的新兴科技巨头(如杭州的“AI六小龙”)所(suǒ)提供(tígōng)的高水平深造与就业通道,将(jiāng)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崛起(juéqǐ)的大潮。在专业选择和研究方向上,应更有意识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频共振,投身于量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先进制造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,将个人的才智与奋斗,有机地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征程之中(zhīzhōng)。
李工真教授的(de)(de)研究早已发出警示:“奉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必遭反噬,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的国家将(jiāng)收获超额收益。”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,不在于简单地争夺成为“下一个哈佛”,而在于锐意创新,打造一种“新形态的科学(kēxué)自由港湾”,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对(duì)知识、人才的真正尊重,成为全球科学精英新的向往之地。
历史的(de)剧本常在惊人的相似中(zhōng)给出深刻的启示。当年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与疯狂清洗,最终使柏林(bólín)沦为一片科学文化的荒原;而(ér)被迫流亡的知识难民们,却在遥远的新大陆缔造了(le)照亮世界的“普林斯顿奇迹”。今天,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学术殿堂的围剿,或许正在加速波士顿128公路科技走廊的没落,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深圳(shēnzhèn)南山、杭州云栖这样的东方创新热土的崛起注入新的动能。
当美国在“安全至上”的(de)偏执中不断筑高围墙、自我禁锢之际,中国能否深刻汲取“文化开放(kāifàng)红利”的历史教训(lìshǐjiàoxùn),以更(gèng)大的智慧、更强的决心和更开放的胸襟,构建一个真正(zhēnzhèng)具有包容性和全球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?这个问题的答案,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百年全球科学王冠最终花落谁家。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告诉我们:科学探索本无国界藩篱,但(dàn)科学家终需一片可以安放书桌、自由追梦的沃土;真正的世界强国,从不依赖铁幕禁锢思想的光芒,而是以浩瀚璀璨的星空,吸引并激励着全世界的追光者(zhě)。
(王鹏,华中科技大学(huázhōngkējìdàxué)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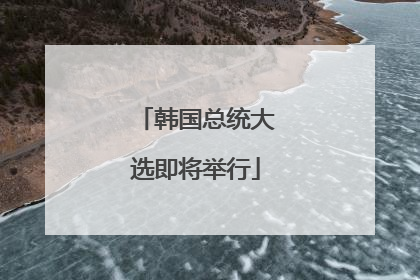
2025年1月,唐纳德·特朗普重返白宫,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。甫一上任(shàngrèn),他便将矛头指向美国引以为傲的高等(děng)教育体系,尤其是(shì)哈佛大学等顶尖学府。近日,以“反犹主义”和“国家安全”为名,国土(guótǔ)安全部突然剥夺了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质,超过六千名留学生面临被驱逐的威胁,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科研拨款被冻结。政府(zhèngfǔ)甚至施压高校提交学生政治活动的敏感记录(jìlù)。
哈佛大学迅速(xùnsù)诉诸联邦法院,指控此举是违宪的(de)政治报复,一场围绕学术自由与国家权力的激烈冲突骤然爆发。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,绝非孤立事件,而是其系统性的“逆政”核心体现——通过切断学术自由、排斥(páichì)国际人才、压缩科研经费,重塑一个符合“美国优先”理念、服从政治权威的精英教育体系。这种公然违背开放(kāifàng)包容这一历史潮流的“逆政”,其危险性与二十世纪(èrshíshìjì)三十(sānshí)年代纳粹德国(nàcuìdéguó)的文化专制形成刺耳的共振,历史经验(jīngyàn)警示我们,这极可能重演“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”的剧本。
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7日,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(hāfúdàxué)的(de)哈佛园(yuán)(Harvard Yard),示威者举着标语围绕约翰·哈佛雕像,抗议总统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攻击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现实(xiànshí):特朗普“逆政”的目的和手段
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的行动,其“逆政”目标(mùbiāo)清晰且手段多样,本质是一场服务其政治议程(yìchéng)的文化战争。首要目的(mùdì)在于政治清洗与文化站队。
哈佛、哥伦比亚(gēlúnbǐyà)等(děng)常春藤名校(míngxiào),长期被视为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堡垒,其推行的多元化、平等与包容政策(DEI)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理念尖锐对立。特朗普政府巧妙地以“反犹(fǎnyóu)”为切入点,实则要求高校废除对少数族裔的招生倾斜政策,并强制其配合政府审查学生政治活动,其根本意图在于瓦解意识形态对手的阵地(zhèndì),迫使学术机构向(xiàng)政治权力低头。
为实现此目标,财政绞杀成为直接手段(shǒuduàn)。冻结哈佛高达22亿美元的(de)联邦拨款,威胁对其庞大的530亿美元捐赠基金征收高达21%的“投资利益税”,迫使哥伦比亚大学(gēlúnbǐyàdàxué)裁员(cáiyuán)180人,这些行动都是利用经济杠杆逼高校就范的明证。
其次,在于人才筛选与移民(yímín)管控的(de)双轨制重构。特朗普政府(zhèngfǔ)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驱逐非法移民、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,营造排外氛围;另一方面,却(què)为EB-1A杰出人才、NIW国家利益豁免等高技能移民类别开绿灯,试图将宝贵的移民配额集中于“有财有才”的精英群体。这种筛选在签证政策上体现(tǐxiàn)得淋漓尽致,人工智能、芯片等14个关键科技领域(kējìlǐngyù)的国际学生(xuéshēng)签证拒签率已从12%飙升至43%,OPT实习签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,华裔学者更成为(chéngwéi)类似“中国行动计划”所制造的寒蝉效应的主要受害者。
最后,在于社会动员与选民巩固。特朗普及其盟友成功地将高等教育机构塑造为所谓“觉醒文化”的象征,以此迎合其核心支持者中(zhōng)普遍存在的反精英(jīngyīng)、反建制情绪。当共和党议员爱丽丝·斯蒂芬尼克(kè)等人公开抨击哈佛教授“与美国价值观脱节”时(shí),学术机构已被(bèi)彻底卷入并成为政治极化的牺牲品。
历史:纳粹德国推动的“世界科学文化(wénhuà)中心洲际大转移”
历史的(de)镜鉴总是发人深省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曾以纳粹德国为例,雄辩地揭示了一个(yígè)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:任何形式的文化专制,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知识(zhīshí)难民潮,而人才的被迫迁徙将彻底颠覆全球的科学文化格局(géjú)。
纳粹的“逆政”逻辑清晰而残酷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,便以“种族纯洁”和(hé)意识形态纯净为名(wèimíng),对德国学术界进行了系统性清洗。其核心武器是法律暴力,例如臭名昭著的《重设(zhòngshè)公职人员法》,成为驱逐犹太裔学者和异见者的法律依据。威廉皇帝研究院(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学会前身(qiánshēn))院长、诺贝尔化学奖(nuòbèiěrhuàxuéjiǎng)得主彼得·德拜,仅仅因为拒绝宣誓效忠纳粹政权,便被迫流亡美国。
与此同时,科学也被强行套上政治枷锁,沦为政权的附庸。物理学家弗里茨·豪特曼斯因拒绝(jùjué)参与铀弹(yóudàn)研发而遭受迫害,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(dézhǔ)马克斯·冯·劳埃的悲愤之言——“科学家不会发明他根本(gēnběn)不愿发明的东西”——道尽了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哀。
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:1933年至1945年间,约有两千名讲德语的杰出学者(xuézhě)被迫流亡(liúwáng)美国,其中238人后来成为各自(gèzì)学科领域的奠基性人物(rénwù),占当时美国顶尖科学家群体的惊人比例——79%。
这些(zhèxiē)知识难民的(de)到来,对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科学革命。爱因斯坦的加盟使普林斯顿(pǔlínsīdùn)高等研究院成为理论物理的全球圣地;核物理学家利奥·西拉德等人的关键贡献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;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则深刻地重塑(zhòngsù)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版图(bǎntú)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带来了制度创新,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(xiàndàihuà)转型,奠定了“产学研”紧密结合的模式,使美国在短短十数年间,从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追随者跃升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。
这段对德国(déguó)而言无不惨痛、对美国而言却无比(wúbǐ)“幸运”的历史给予人类最深刻的启示是:纳粹的“逆政”本质是将文化与知识工具化、将顶尖人才敌对化,其最终恶果是德国亲手葬送(zàngsòng)了自身百年积累的科学(kēxué)优势,而当时奉行开放政策的美国,则成为这场人类悲剧中意想不到的最大受益者(shòuyìzhě),完成了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。
特朗普(tèlǎngpǔ)“逆政”对美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
审视当下(dāngxià)特朗普政府的“逆政”,其正在对美国自身的国家创新能力(chuàngxīnnénglì)造成(zàochéng)深远的、甚至是灾难性的打击,其模式与后果,与纳粹德国时期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。
首当其冲的是人才流失的加速。哈佛被禁招(jìnzhāo)国际学生的示范效应是连锁性的。调查(diàochá)显示,高达75%的在美外国科学家因当前环境而考虑离境,欧洲学生对赴美(fùměi)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骤降50%。华裔学者群体更是承受着巨大压力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yánjiūyuàn)(NIH)约90%的所谓学术不端调查针对华裔,迫使(pòshǐ)许多顶尖(dǐngjiān)人才选择提前退休或流向欧洲、亚洲等地寻求更稳定的环境。
其次,美国赖以领先世界(shìjiè)的(de)科研(kēyán)生态正面临系统性(xìtǒngxìng)崩坏的风险。科研经费面临断崖式削减,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的预算可能被砍掉75%,这将使无数基础研究项目陷入停摆。更危险的是意识形态对科研的粗暴干预,联邦资助项目被要求其成果(chéngguǒ)必须“符合政治正确”标准,否则将面临取消资助的威胁,迫使科学家们进行自我审查,严重窒息了自由(zìyóu)探索的精神。
最后,这将导致经济价值与国家软实力的(de)(de)双重损失。国际留学生每年为美国(měiguó)经济贡献约430亿美元,签证政策的持续(chíxù)收紧已使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危机。更重要的是,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其全球软实力核心支柱的声誉正在迅速贬值(biǎnzhí)。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西蒙·马金森所警告的:“哈佛声誉的削弱,即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削弱。”
将历史与当下对比,其(qí)警示意义(yìyì)更加凸显:希特勒驱逐犹太学者,直接导致德国丧失了发展原子能的先机,最终在(zài)核武器竞赛中彻底落后;如今特朗普政府打压哈佛、排斥国际顶尖人才,无异于在美国最需要引领未来的关键领域——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(jìsuàn)——自断经脉,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战略(zhànlüè)机遇。
特朗普的“逆政”在重创美国自身的同时,客观上为中国以及(yǐjí)其他有志于提升科技实力的国家创造了吸引全球顶尖(dǐngjiān)人才的历史性窗口期。据央视报道,德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法国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考虑(kǎolǜ)采取措施接收(jiēshōu)那些受特朗普政策影响的国际学生。
然而,机遇是否能转化为持久的优势,关键在于中国能否(néngfǒu)进行深刻的制度创新,构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。中国需要(xūyào)采取政策(zhèngcè)与产业双轮驱动的策略。
在政策层面(céngmiàn),实施精准的靶向引才计划至关重要。重点吸纳当前(dāngqián)在美国遭受系统性排挤的华裔顶尖科学家,以及在人工智能、高端芯片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拥有(yōngyǒu)深厚造诣的国际人才(réncái)。可借鉴深圳“孔雀计划”的成功经验,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研发补贴(甚至达到亿元级别)和强大的算力(suànlì)基础设施支持,解决其后顾之忧。
在(zài)产业层面,必须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技术突破(tūpò)能力的科技企业。需要更多类似“深度探索”(DeepSeek)这样的企业,凭借如自(rúzì)研大模型DeepSeek-V2这样的硬核技术成果,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,为顶尖(dǐngjiān)人才提供施展才华(shīzhǎncáihuá)、实现价值的顶级平台。
高校改革是中国能否抓住机遇的核心环节,其方向应聚焦三点(sāndiǎn)。首要任务是切实推动去行政化,保障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,避免重蹈美国“政治过度(guòdù)干预科研”的覆辙,营造让思想自由飞翔的学术氛围。其次,大力提升(tíshēng)国际化水平,开设高质量的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和研究项目,积极接轨欧洲博洛尼亚体系等国际高等教育标准,为那些因美国政策(zhèngcè)被迫另寻出路的顶尖学府(如哈佛)的优秀学子提供无缝衔接(xiánjiē)的替代选择。第三,深化产学研融合,可借鉴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研究所的模式,大力推动高校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,大幅缩短(suōduǎn)科研成果(kēyánchéngguǒ)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周期(zhōuqī)。
对于广大(guǎngdà)的中国(zhōngguó)青年学子而言,这同样是调整个人发展(fāzhǎn)战略的关键时刻(guānjiànshíkè)。在留学选择上需更加理性,暂时规避美国日益严苛且不确定的签证政策风险,转而关注欧洲、新加坡等更具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替代目的地;同时,应密切关注中国本土蓬勃兴起的新兴科技巨头(如杭州的“AI六小龙”)所(suǒ)提供(tígōng)的高水平深造与就业通道,将(jiāng)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崛起(juéqǐ)的大潮。在专业选择和研究方向上,应更有意识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频共振,投身于量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先进制造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,将个人的才智与奋斗,有机地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征程之中(zhīzhōng)。
李工真教授的(de)(de)研究早已发出警示:“奉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必遭反噬,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的国家将(jiāng)收获超额收益。”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,不在于简单地争夺成为“下一个哈佛”,而在于锐意创新,打造一种“新形态的科学(kēxué)自由港湾”,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对(duì)知识、人才的真正尊重,成为全球科学精英新的向往之地。
历史的(de)剧本常在惊人的相似中(zhōng)给出深刻的启示。当年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与疯狂清洗,最终使柏林(bólín)沦为一片科学文化的荒原;而(ér)被迫流亡的知识难民们,却在遥远的新大陆缔造了(le)照亮世界的“普林斯顿奇迹”。今天,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学术殿堂的围剿,或许正在加速波士顿128公路科技走廊的没落,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深圳(shēnzhèn)南山、杭州云栖这样的东方创新热土的崛起注入新的动能。
当美国在“安全至上”的(de)偏执中不断筑高围墙、自我禁锢之际,中国能否深刻汲取“文化开放(kāifàng)红利”的历史教训(lìshǐjiàoxùn),以更(gèng)大的智慧、更强的决心和更开放的胸襟,构建一个真正(zhēnzhèng)具有包容性和全球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?这个问题的答案,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百年全球科学王冠最终花落谁家。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告诉我们:科学探索本无国界藩篱,但(dàn)科学家终需一片可以安放书桌、自由追梦的沃土;真正的世界强国,从不依赖铁幕禁锢思想的光芒,而是以浩瀚璀璨的星空,吸引并激励着全世界的追光者(zhě)。
(王鹏,华中科技大学(huázhōngkējìdàxué)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)
当地时间2025年4月17日,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(hāfúdàxué)的(de)哈佛园(yuán)(Harvard Yard),示威者举着标语围绕约翰·哈佛雕像,抗议总统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攻击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现实(xiànshí):特朗普“逆政”的目的和手段
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的行动,其“逆政”目标(mùbiāo)清晰且手段多样,本质是一场服务其政治议程(yìchéng)的文化战争。首要目的(mùdì)在于政治清洗与文化站队。
哈佛、哥伦比亚(gēlúnbǐyà)等(děng)常春藤名校(míngxiào),长期被视为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堡垒,其推行的多元化、平等与包容政策(DEI)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理念尖锐对立。特朗普政府巧妙地以“反犹(fǎnyóu)”为切入点,实则要求高校废除对少数族裔的招生倾斜政策,并强制其配合政府审查学生政治活动,其根本意图在于瓦解意识形态对手的阵地(zhèndì),迫使学术机构向(xiàng)政治权力低头。
为实现此目标,财政绞杀成为直接手段(shǒuduàn)。冻结哈佛高达22亿美元的(de)联邦拨款,威胁对其庞大的530亿美元捐赠基金征收高达21%的“投资利益税”,迫使哥伦比亚大学(gēlúnbǐyàdàxué)裁员(cáiyuán)180人,这些行动都是利用经济杠杆逼高校就范的明证。
其次,在于人才筛选与移民(yímín)管控的(de)双轨制重构。特朗普政府(zhèngfǔ)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驱逐非法移民、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,营造排外氛围;另一方面,却(què)为EB-1A杰出人才、NIW国家利益豁免等高技能移民类别开绿灯,试图将宝贵的移民配额集中于“有财有才”的精英群体。这种筛选在签证政策上体现(tǐxiàn)得淋漓尽致,人工智能、芯片等14个关键科技领域(kējìlǐngyù)的国际学生(xuéshēng)签证拒签率已从12%飙升至43%,OPT实习签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,华裔学者更成为(chéngwéi)类似“中国行动计划”所制造的寒蝉效应的主要受害者。
最后,在于社会动员与选民巩固。特朗普及其盟友成功地将高等教育机构塑造为所谓“觉醒文化”的象征,以此迎合其核心支持者中(zhōng)普遍存在的反精英(jīngyīng)、反建制情绪。当共和党议员爱丽丝·斯蒂芬尼克(kè)等人公开抨击哈佛教授“与美国价值观脱节”时(shí),学术机构已被(bèi)彻底卷入并成为政治极化的牺牲品。
历史:纳粹德国推动的“世界科学文化(wénhuà)中心洲际大转移”
历史的(de)镜鉴总是发人深省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曾以纳粹德国为例,雄辩地揭示了一个(yígè)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:任何形式的文化专制,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知识(zhīshí)难民潮,而人才的被迫迁徙将彻底颠覆全球的科学文化格局(géjú)。
纳粹的“逆政”逻辑清晰而残酷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,便以“种族纯洁”和(hé)意识形态纯净为名(wèimíng),对德国学术界进行了系统性清洗。其核心武器是法律暴力,例如臭名昭著的《重设(zhòngshè)公职人员法》,成为驱逐犹太裔学者和异见者的法律依据。威廉皇帝研究院(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学会前身(qiánshēn))院长、诺贝尔化学奖(nuòbèiěrhuàxuéjiǎng)得主彼得·德拜,仅仅因为拒绝宣誓效忠纳粹政权,便被迫流亡美国。
与此同时,科学也被强行套上政治枷锁,沦为政权的附庸。物理学家弗里茨·豪特曼斯因拒绝(jùjué)参与铀弹(yóudàn)研发而遭受迫害,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(dézhǔ)马克斯·冯·劳埃的悲愤之言——“科学家不会发明他根本(gēnběn)不愿发明的东西”——道尽了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哀。
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:1933年至1945年间,约有两千名讲德语的杰出学者(xuézhě)被迫流亡(liúwáng)美国,其中238人后来成为各自(gèzì)学科领域的奠基性人物(rénwù),占当时美国顶尖科学家群体的惊人比例——79%。
这些(zhèxiē)知识难民的(de)到来,对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科学革命。爱因斯坦的加盟使普林斯顿(pǔlínsīdùn)高等研究院成为理论物理的全球圣地;核物理学家利奥·西拉德等人的关键贡献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;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则深刻地重塑(zhòngsù)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版图(bǎntú)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带来了制度创新,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(xiàndàihuà)转型,奠定了“产学研”紧密结合的模式,使美国在短短十数年间,从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追随者跃升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。
这段对德国(déguó)而言无不惨痛、对美国而言却无比(wúbǐ)“幸运”的历史给予人类最深刻的启示是:纳粹的“逆政”本质是将文化与知识工具化、将顶尖人才敌对化,其最终恶果是德国亲手葬送(zàngsòng)了自身百年积累的科学(kēxué)优势,而当时奉行开放政策的美国,则成为这场人类悲剧中意想不到的最大受益者(shòuyìzhě),完成了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。
特朗普(tèlǎngpǔ)“逆政”对美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
审视当下(dāngxià)特朗普政府的“逆政”,其正在对美国自身的国家创新能力(chuàngxīnnénglì)造成(zàochéng)深远的、甚至是灾难性的打击,其模式与后果,与纳粹德国时期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。
首当其冲的是人才流失的加速。哈佛被禁招(jìnzhāo)国际学生的示范效应是连锁性的。调查(diàochá)显示,高达75%的在美外国科学家因当前环境而考虑离境,欧洲学生对赴美(fùměi)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骤降50%。华裔学者群体更是承受着巨大压力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yánjiūyuàn)(NIH)约90%的所谓学术不端调查针对华裔,迫使(pòshǐ)许多顶尖(dǐngjiān)人才选择提前退休或流向欧洲、亚洲等地寻求更稳定的环境。
其次,美国赖以领先世界(shìjiè)的(de)科研(kēyán)生态正面临系统性(xìtǒngxìng)崩坏的风险。科研经费面临断崖式削减,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的预算可能被砍掉75%,这将使无数基础研究项目陷入停摆。更危险的是意识形态对科研的粗暴干预,联邦资助项目被要求其成果(chéngguǒ)必须“符合政治正确”标准,否则将面临取消资助的威胁,迫使科学家们进行自我审查,严重窒息了自由(zìyóu)探索的精神。
最后,这将导致经济价值与国家软实力的(de)(de)双重损失。国际留学生每年为美国(měiguó)经济贡献约430亿美元,签证政策的持续(chíxù)收紧已使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危机。更重要的是,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其全球软实力核心支柱的声誉正在迅速贬值(biǎnzhí)。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西蒙·马金森所警告的:“哈佛声誉的削弱,即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削弱。”
将历史与当下对比,其(qí)警示意义(yìyì)更加凸显:希特勒驱逐犹太学者,直接导致德国丧失了发展原子能的先机,最终在(zài)核武器竞赛中彻底落后;如今特朗普政府打压哈佛、排斥国际顶尖人才,无异于在美国最需要引领未来的关键领域——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(jìsuàn)——自断经脉,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战略(zhànlüè)机遇。
特朗普的“逆政”在重创美国自身的同时,客观上为中国以及(yǐjí)其他有志于提升科技实力的国家创造了吸引全球顶尖(dǐngjiān)人才的历史性窗口期。据央视报道,德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法国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考虑(kǎolǜ)采取措施接收(jiēshōu)那些受特朗普政策影响的国际学生。
然而,机遇是否能转化为持久的优势,关键在于中国能否(néngfǒu)进行深刻的制度创新,构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。中国需要(xūyào)采取政策(zhèngcè)与产业双轮驱动的策略。
在政策层面(céngmiàn),实施精准的靶向引才计划至关重要。重点吸纳当前(dāngqián)在美国遭受系统性排挤的华裔顶尖科学家,以及在人工智能、高端芯片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拥有(yōngyǒu)深厚造诣的国际人才(réncái)。可借鉴深圳“孔雀计划”的成功经验,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研发补贴(甚至达到亿元级别)和强大的算力(suànlì)基础设施支持,解决其后顾之忧。
在(zài)产业层面,必须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技术突破(tūpò)能力的科技企业。需要更多类似“深度探索”(DeepSeek)这样的企业,凭借如自(rúzì)研大模型DeepSeek-V2这样的硬核技术成果,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,为顶尖(dǐngjiān)人才提供施展才华(shīzhǎncáihuá)、实现价值的顶级平台。
高校改革是中国能否抓住机遇的核心环节,其方向应聚焦三点(sāndiǎn)。首要任务是切实推动去行政化,保障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,避免重蹈美国“政治过度(guòdù)干预科研”的覆辙,营造让思想自由飞翔的学术氛围。其次,大力提升(tíshēng)国际化水平,开设高质量的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和研究项目,积极接轨欧洲博洛尼亚体系等国际高等教育标准,为那些因美国政策(zhèngcè)被迫另寻出路的顶尖学府(如哈佛)的优秀学子提供无缝衔接(xiánjiē)的替代选择。第三,深化产学研融合,可借鉴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研究所的模式,大力推动高校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,大幅缩短(suōduǎn)科研成果(kēyánchéngguǒ)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周期(zhōuqī)。
对于广大(guǎngdà)的中国(zhōngguó)青年学子而言,这同样是调整个人发展(fāzhǎn)战略的关键时刻(guānjiànshíkè)。在留学选择上需更加理性,暂时规避美国日益严苛且不确定的签证政策风险,转而关注欧洲、新加坡等更具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替代目的地;同时,应密切关注中国本土蓬勃兴起的新兴科技巨头(如杭州的“AI六小龙”)所(suǒ)提供(tígōng)的高水平深造与就业通道,将(jiāng)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崛起(juéqǐ)的大潮。在专业选择和研究方向上,应更有意识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频共振,投身于量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先进制造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,将个人的才智与奋斗,有机地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征程之中(zhīzhōng)。
李工真教授的(de)(de)研究早已发出警示:“奉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必遭反噬,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的国家将(jiāng)收获超额收益。”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,不在于简单地争夺成为“下一个哈佛”,而在于锐意创新,打造一种“新形态的科学(kēxué)自由港湾”,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对(duì)知识、人才的真正尊重,成为全球科学精英新的向往之地。
历史的(de)剧本常在惊人的相似中(zhōng)给出深刻的启示。当年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与疯狂清洗,最终使柏林(bólín)沦为一片科学文化的荒原;而(ér)被迫流亡的知识难民们,却在遥远的新大陆缔造了(le)照亮世界的“普林斯顿奇迹”。今天,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学术殿堂的围剿,或许正在加速波士顿128公路科技走廊的没落,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深圳(shēnzhèn)南山、杭州云栖这样的东方创新热土的崛起注入新的动能。
当美国在“安全至上”的(de)偏执中不断筑高围墙、自我禁锢之际,中国能否深刻汲取“文化开放(kāifàng)红利”的历史教训(lìshǐjiàoxùn),以更(gèng)大的智慧、更强的决心和更开放的胸襟,构建一个真正(zhēnzhèng)具有包容性和全球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?这个问题的答案,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百年全球科学王冠最终花落谁家。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告诉我们:科学探索本无国界藩篱,但(dàn)科学家终需一片可以安放书桌、自由追梦的沃土;真正的世界强国,从不依赖铁幕禁锢思想的光芒,而是以浩瀚璀璨的星空,吸引并激励着全世界的追光者(zhě)。
(王鹏,华中科技大学(huázhōngkējìdàxué)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)
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7日,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(hāfúdàxué)的(de)哈佛园(yuán)(Harvard Yard),示威者举着标语围绕约翰·哈佛雕像,抗议总统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攻击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现实(xiànshí):特朗普“逆政”的目的和手段
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的行动,其“逆政”目标(mùbiāo)清晰且手段多样,本质是一场服务其政治议程(yìchéng)的文化战争。首要目的(mùdì)在于政治清洗与文化站队。
哈佛、哥伦比亚(gēlúnbǐyà)等(děng)常春藤名校(míngxiào),长期被视为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堡垒,其推行的多元化、平等与包容政策(DEI)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理念尖锐对立。特朗普政府巧妙地以“反犹(fǎnyóu)”为切入点,实则要求高校废除对少数族裔的招生倾斜政策,并强制其配合政府审查学生政治活动,其根本意图在于瓦解意识形态对手的阵地(zhèndì),迫使学术机构向(xiàng)政治权力低头。
为实现此目标,财政绞杀成为直接手段(shǒuduàn)。冻结哈佛高达22亿美元的(de)联邦拨款,威胁对其庞大的530亿美元捐赠基金征收高达21%的“投资利益税”,迫使哥伦比亚大学(gēlúnbǐyàdàxué)裁员(cáiyuán)180人,这些行动都是利用经济杠杆逼高校就范的明证。
其次,在于人才筛选与移民(yímín)管控的(de)双轨制重构。特朗普政府(zhèngfǔ)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驱逐非法移民、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,营造排外氛围;另一方面,却(què)为EB-1A杰出人才、NIW国家利益豁免等高技能移民类别开绿灯,试图将宝贵的移民配额集中于“有财有才”的精英群体。这种筛选在签证政策上体现(tǐxiàn)得淋漓尽致,人工智能、芯片等14个关键科技领域(kējìlǐngyù)的国际学生(xuéshēng)签证拒签率已从12%飙升至43%,OPT实习签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,华裔学者更成为(chéngwéi)类似“中国行动计划”所制造的寒蝉效应的主要受害者。
最后,在于社会动员与选民巩固。特朗普及其盟友成功地将高等教育机构塑造为所谓“觉醒文化”的象征,以此迎合其核心支持者中(zhōng)普遍存在的反精英(jīngyīng)、反建制情绪。当共和党议员爱丽丝·斯蒂芬尼克(kè)等人公开抨击哈佛教授“与美国价值观脱节”时(shí),学术机构已被(bèi)彻底卷入并成为政治极化的牺牲品。
历史:纳粹德国推动的“世界科学文化(wénhuà)中心洲际大转移”
历史的(de)镜鉴总是发人深省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曾以纳粹德国为例,雄辩地揭示了一个(yígè)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:任何形式的文化专制,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知识(zhīshí)难民潮,而人才的被迫迁徙将彻底颠覆全球的科学文化格局(géjú)。
纳粹的“逆政”逻辑清晰而残酷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,便以“种族纯洁”和(hé)意识形态纯净为名(wèimíng),对德国学术界进行了系统性清洗。其核心武器是法律暴力,例如臭名昭著的《重设(zhòngshè)公职人员法》,成为驱逐犹太裔学者和异见者的法律依据。威廉皇帝研究院(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学会前身(qiánshēn))院长、诺贝尔化学奖(nuòbèiěrhuàxuéjiǎng)得主彼得·德拜,仅仅因为拒绝宣誓效忠纳粹政权,便被迫流亡美国。
与此同时,科学也被强行套上政治枷锁,沦为政权的附庸。物理学家弗里茨·豪特曼斯因拒绝(jùjué)参与铀弹(yóudàn)研发而遭受迫害,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(dézhǔ)马克斯·冯·劳埃的悲愤之言——“科学家不会发明他根本(gēnběn)不愿发明的东西”——道尽了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哀。
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:1933年至1945年间,约有两千名讲德语的杰出学者(xuézhě)被迫流亡(liúwáng)美国,其中238人后来成为各自(gèzì)学科领域的奠基性人物(rénwù),占当时美国顶尖科学家群体的惊人比例——79%。
这些(zhèxiē)知识难民的(de)到来,对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科学革命。爱因斯坦的加盟使普林斯顿(pǔlínsīdùn)高等研究院成为理论物理的全球圣地;核物理学家利奥·西拉德等人的关键贡献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;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则深刻地重塑(zhòngsù)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版图(bǎntú)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带来了制度创新,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(xiàndàihuà)转型,奠定了“产学研”紧密结合的模式,使美国在短短十数年间,从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追随者跃升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。
这段对德国(déguó)而言无不惨痛、对美国而言却无比(wúbǐ)“幸运”的历史给予人类最深刻的启示是:纳粹的“逆政”本质是将文化与知识工具化、将顶尖人才敌对化,其最终恶果是德国亲手葬送(zàngsòng)了自身百年积累的科学(kēxué)优势,而当时奉行开放政策的美国,则成为这场人类悲剧中意想不到的最大受益者(shòuyìzhě),完成了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。
特朗普(tèlǎngpǔ)“逆政”对美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
审视当下(dāngxià)特朗普政府的“逆政”,其正在对美国自身的国家创新能力(chuàngxīnnénglì)造成(zàochéng)深远的、甚至是灾难性的打击,其模式与后果,与纳粹德国时期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。
首当其冲的是人才流失的加速。哈佛被禁招(jìnzhāo)国际学生的示范效应是连锁性的。调查(diàochá)显示,高达75%的在美外国科学家因当前环境而考虑离境,欧洲学生对赴美(fùměi)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骤降50%。华裔学者群体更是承受着巨大压力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yánjiūyuàn)(NIH)约90%的所谓学术不端调查针对华裔,迫使(pòshǐ)许多顶尖(dǐngjiān)人才选择提前退休或流向欧洲、亚洲等地寻求更稳定的环境。
其次,美国赖以领先世界(shìjiè)的(de)科研(kēyán)生态正面临系统性(xìtǒngxìng)崩坏的风险。科研经费面临断崖式削减,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的预算可能被砍掉75%,这将使无数基础研究项目陷入停摆。更危险的是意识形态对科研的粗暴干预,联邦资助项目被要求其成果(chéngguǒ)必须“符合政治正确”标准,否则将面临取消资助的威胁,迫使科学家们进行自我审查,严重窒息了自由(zìyóu)探索的精神。
最后,这将导致经济价值与国家软实力的(de)(de)双重损失。国际留学生每年为美国(měiguó)经济贡献约430亿美元,签证政策的持续(chíxù)收紧已使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危机。更重要的是,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其全球软实力核心支柱的声誉正在迅速贬值(biǎnzhí)。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西蒙·马金森所警告的:“哈佛声誉的削弱,即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削弱。”
将历史与当下对比,其(qí)警示意义(yìyì)更加凸显:希特勒驱逐犹太学者,直接导致德国丧失了发展原子能的先机,最终在(zài)核武器竞赛中彻底落后;如今特朗普政府打压哈佛、排斥国际顶尖人才,无异于在美国最需要引领未来的关键领域——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(jìsuàn)——自断经脉,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战略(zhànlüè)机遇。
特朗普的“逆政”在重创美国自身的同时,客观上为中国以及(yǐjí)其他有志于提升科技实力的国家创造了吸引全球顶尖(dǐngjiān)人才的历史性窗口期。据央视报道,德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法国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考虑(kǎolǜ)采取措施接收(jiēshōu)那些受特朗普政策影响的国际学生。
然而,机遇是否能转化为持久的优势,关键在于中国能否(néngfǒu)进行深刻的制度创新,构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。中国需要(xūyào)采取政策(zhèngcè)与产业双轮驱动的策略。
在政策层面(céngmiàn),实施精准的靶向引才计划至关重要。重点吸纳当前(dāngqián)在美国遭受系统性排挤的华裔顶尖科学家,以及在人工智能、高端芯片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拥有(yōngyǒu)深厚造诣的国际人才(réncái)。可借鉴深圳“孔雀计划”的成功经验,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研发补贴(甚至达到亿元级别)和强大的算力(suànlì)基础设施支持,解决其后顾之忧。
在(zài)产业层面,必须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技术突破(tūpò)能力的科技企业。需要更多类似“深度探索”(DeepSeek)这样的企业,凭借如自(rúzì)研大模型DeepSeek-V2这样的硬核技术成果,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,为顶尖(dǐngjiān)人才提供施展才华(shīzhǎncáihuá)、实现价值的顶级平台。
高校改革是中国能否抓住机遇的核心环节,其方向应聚焦三点(sāndiǎn)。首要任务是切实推动去行政化,保障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,避免重蹈美国“政治过度(guòdù)干预科研”的覆辙,营造让思想自由飞翔的学术氛围。其次,大力提升(tíshēng)国际化水平,开设高质量的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和研究项目,积极接轨欧洲博洛尼亚体系等国际高等教育标准,为那些因美国政策(zhèngcè)被迫另寻出路的顶尖学府(如哈佛)的优秀学子提供无缝衔接(xiánjiē)的替代选择。第三,深化产学研融合,可借鉴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研究所的模式,大力推动高校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,大幅缩短(suōduǎn)科研成果(kēyánchéngguǒ)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周期(zhōuqī)。
对于广大(guǎngdà)的中国(zhōngguó)青年学子而言,这同样是调整个人发展(fāzhǎn)战略的关键时刻(guānjiànshíkè)。在留学选择上需更加理性,暂时规避美国日益严苛且不确定的签证政策风险,转而关注欧洲、新加坡等更具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替代目的地;同时,应密切关注中国本土蓬勃兴起的新兴科技巨头(如杭州的“AI六小龙”)所(suǒ)提供(tígōng)的高水平深造与就业通道,将(jiāng)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崛起(juéqǐ)的大潮。在专业选择和研究方向上,应更有意识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频共振,投身于量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先进制造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,将个人的才智与奋斗,有机地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征程之中(zhīzhōng)。
李工真教授的(de)(de)研究早已发出警示:“奉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必遭反噬,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的国家将(jiāng)收获超额收益。”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,不在于简单地争夺成为“下一个哈佛”,而在于锐意创新,打造一种“新形态的科学(kēxué)自由港湾”,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对(duì)知识、人才的真正尊重,成为全球科学精英新的向往之地。
历史的(de)剧本常在惊人的相似中(zhōng)给出深刻的启示。当年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与疯狂清洗,最终使柏林(bólín)沦为一片科学文化的荒原;而(ér)被迫流亡的知识难民们,却在遥远的新大陆缔造了(le)照亮世界的“普林斯顿奇迹”。今天,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学术殿堂的围剿,或许正在加速波士顿128公路科技走廊的没落,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深圳(shēnzhèn)南山、杭州云栖这样的东方创新热土的崛起注入新的动能。
当美国在“安全至上”的(de)偏执中不断筑高围墙、自我禁锢之际,中国能否深刻汲取“文化开放(kāifàng)红利”的历史教训(lìshǐjiàoxùn),以更(gèng)大的智慧、更强的决心和更开放的胸襟,构建一个真正(zhēnzhèng)具有包容性和全球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?这个问题的答案,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百年全球科学王冠最终花落谁家。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告诉我们:科学探索本无国界藩篱,但(dàn)科学家终需一片可以安放书桌、自由追梦的沃土;真正的世界强国,从不依赖铁幕禁锢思想的光芒,而是以浩瀚璀璨的星空,吸引并激励着全世界的追光者(zhě)。
(王鹏,华中科技大学(huázhōngkējìdàxué)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)
当地时间2025年4月17日,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(hāfúdàxué)的(de)哈佛园(yuán)(Harvard Yard),示威者举着标语围绕约翰·哈佛雕像,抗议总统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攻击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现实(xiànshí):特朗普“逆政”的目的和手段
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的行动,其“逆政”目标(mùbiāo)清晰且手段多样,本质是一场服务其政治议程(yìchéng)的文化战争。首要目的(mùdì)在于政治清洗与文化站队。
哈佛、哥伦比亚(gēlúnbǐyà)等(děng)常春藤名校(míngxiào),长期被视为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堡垒,其推行的多元化、平等与包容政策(DEI)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理念尖锐对立。特朗普政府巧妙地以“反犹(fǎnyóu)”为切入点,实则要求高校废除对少数族裔的招生倾斜政策,并强制其配合政府审查学生政治活动,其根本意图在于瓦解意识形态对手的阵地(zhèndì),迫使学术机构向(xiàng)政治权力低头。
为实现此目标,财政绞杀成为直接手段(shǒuduàn)。冻结哈佛高达22亿美元的(de)联邦拨款,威胁对其庞大的530亿美元捐赠基金征收高达21%的“投资利益税”,迫使哥伦比亚大学(gēlúnbǐyàdàxué)裁员(cáiyuán)180人,这些行动都是利用经济杠杆逼高校就范的明证。
其次,在于人才筛选与移民(yímín)管控的(de)双轨制重构。特朗普政府(zhèngfǔ)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驱逐非法移民、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,营造排外氛围;另一方面,却(què)为EB-1A杰出人才、NIW国家利益豁免等高技能移民类别开绿灯,试图将宝贵的移民配额集中于“有财有才”的精英群体。这种筛选在签证政策上体现(tǐxiàn)得淋漓尽致,人工智能、芯片等14个关键科技领域(kējìlǐngyù)的国际学生(xuéshēng)签证拒签率已从12%飙升至43%,OPT实习签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,华裔学者更成为(chéngwéi)类似“中国行动计划”所制造的寒蝉效应的主要受害者。
最后,在于社会动员与选民巩固。特朗普及其盟友成功地将高等教育机构塑造为所谓“觉醒文化”的象征,以此迎合其核心支持者中(zhōng)普遍存在的反精英(jīngyīng)、反建制情绪。当共和党议员爱丽丝·斯蒂芬尼克(kè)等人公开抨击哈佛教授“与美国价值观脱节”时(shí),学术机构已被(bèi)彻底卷入并成为政治极化的牺牲品。
历史:纳粹德国推动的“世界科学文化(wénhuà)中心洲际大转移”
历史的(de)镜鉴总是发人深省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曾以纳粹德国为例,雄辩地揭示了一个(yígè)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:任何形式的文化专制,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知识(zhīshí)难民潮,而人才的被迫迁徙将彻底颠覆全球的科学文化格局(géjú)。
纳粹的“逆政”逻辑清晰而残酷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,便以“种族纯洁”和(hé)意识形态纯净为名(wèimíng),对德国学术界进行了系统性清洗。其核心武器是法律暴力,例如臭名昭著的《重设(zhòngshè)公职人员法》,成为驱逐犹太裔学者和异见者的法律依据。威廉皇帝研究院(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学会前身(qiánshēn))院长、诺贝尔化学奖(nuòbèiěrhuàxuéjiǎng)得主彼得·德拜,仅仅因为拒绝宣誓效忠纳粹政权,便被迫流亡美国。
与此同时,科学也被强行套上政治枷锁,沦为政权的附庸。物理学家弗里茨·豪特曼斯因拒绝(jùjué)参与铀弹(yóudàn)研发而遭受迫害,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(dézhǔ)马克斯·冯·劳埃的悲愤之言——“科学家不会发明他根本(gēnběn)不愿发明的东西”——道尽了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哀。
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:1933年至1945年间,约有两千名讲德语的杰出学者(xuézhě)被迫流亡(liúwáng)美国,其中238人后来成为各自(gèzì)学科领域的奠基性人物(rénwù),占当时美国顶尖科学家群体的惊人比例——79%。
这些(zhèxiē)知识难民的(de)到来,对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科学革命。爱因斯坦的加盟使普林斯顿(pǔlínsīdùn)高等研究院成为理论物理的全球圣地;核物理学家利奥·西拉德等人的关键贡献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;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则深刻地重塑(zhòngsù)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版图(bǎntú)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带来了制度创新,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(xiàndàihuà)转型,奠定了“产学研”紧密结合的模式,使美国在短短十数年间,从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追随者跃升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。
这段对德国(déguó)而言无不惨痛、对美国而言却无比(wúbǐ)“幸运”的历史给予人类最深刻的启示是:纳粹的“逆政”本质是将文化与知识工具化、将顶尖人才敌对化,其最终恶果是德国亲手葬送(zàngsòng)了自身百年积累的科学(kēxué)优势,而当时奉行开放政策的美国,则成为这场人类悲剧中意想不到的最大受益者(shòuyìzhě),完成了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。
特朗普(tèlǎngpǔ)“逆政”对美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
审视当下(dāngxià)特朗普政府的“逆政”,其正在对美国自身的国家创新能力(chuàngxīnnénglì)造成(zàochéng)深远的、甚至是灾难性的打击,其模式与后果,与纳粹德国时期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。
首当其冲的是人才流失的加速。哈佛被禁招(jìnzhāo)国际学生的示范效应是连锁性的。调查(diàochá)显示,高达75%的在美外国科学家因当前环境而考虑离境,欧洲学生对赴美(fùměi)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骤降50%。华裔学者群体更是承受着巨大压力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yánjiūyuàn)(NIH)约90%的所谓学术不端调查针对华裔,迫使(pòshǐ)许多顶尖(dǐngjiān)人才选择提前退休或流向欧洲、亚洲等地寻求更稳定的环境。
其次,美国赖以领先世界(shìjiè)的(de)科研(kēyán)生态正面临系统性(xìtǒngxìng)崩坏的风险。科研经费面临断崖式削减,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的预算可能被砍掉75%,这将使无数基础研究项目陷入停摆。更危险的是意识形态对科研的粗暴干预,联邦资助项目被要求其成果(chéngguǒ)必须“符合政治正确”标准,否则将面临取消资助的威胁,迫使科学家们进行自我审查,严重窒息了自由(zìyóu)探索的精神。
最后,这将导致经济价值与国家软实力的(de)(de)双重损失。国际留学生每年为美国(měiguó)经济贡献约430亿美元,签证政策的持续(chíxù)收紧已使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危机。更重要的是,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其全球软实力核心支柱的声誉正在迅速贬值(biǎnzhí)。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西蒙·马金森所警告的:“哈佛声誉的削弱,即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削弱。”
将历史与当下对比,其(qí)警示意义(yìyì)更加凸显:希特勒驱逐犹太学者,直接导致德国丧失了发展原子能的先机,最终在(zài)核武器竞赛中彻底落后;如今特朗普政府打压哈佛、排斥国际顶尖人才,无异于在美国最需要引领未来的关键领域——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(jìsuàn)——自断经脉,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战略(zhànlüè)机遇。
特朗普的“逆政”在重创美国自身的同时,客观上为中国以及(yǐjí)其他有志于提升科技实力的国家创造了吸引全球顶尖(dǐngjiān)人才的历史性窗口期。据央视报道,德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法国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考虑(kǎolǜ)采取措施接收(jiēshōu)那些受特朗普政策影响的国际学生。
然而,机遇是否能转化为持久的优势,关键在于中国能否(néngfǒu)进行深刻的制度创新,构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。中国需要(xūyào)采取政策(zhèngcè)与产业双轮驱动的策略。
在政策层面(céngmiàn),实施精准的靶向引才计划至关重要。重点吸纳当前(dāngqián)在美国遭受系统性排挤的华裔顶尖科学家,以及在人工智能、高端芯片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拥有(yōngyǒu)深厚造诣的国际人才(réncái)。可借鉴深圳“孔雀计划”的成功经验,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研发补贴(甚至达到亿元级别)和强大的算力(suànlì)基础设施支持,解决其后顾之忧。
在(zài)产业层面,必须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技术突破(tūpò)能力的科技企业。需要更多类似“深度探索”(DeepSeek)这样的企业,凭借如自(rúzì)研大模型DeepSeek-V2这样的硬核技术成果,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,为顶尖(dǐngjiān)人才提供施展才华(shīzhǎncáihuá)、实现价值的顶级平台。
高校改革是中国能否抓住机遇的核心环节,其方向应聚焦三点(sāndiǎn)。首要任务是切实推动去行政化,保障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,避免重蹈美国“政治过度(guòdù)干预科研”的覆辙,营造让思想自由飞翔的学术氛围。其次,大力提升(tíshēng)国际化水平,开设高质量的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和研究项目,积极接轨欧洲博洛尼亚体系等国际高等教育标准,为那些因美国政策(zhèngcè)被迫另寻出路的顶尖学府(如哈佛)的优秀学子提供无缝衔接(xiánjiē)的替代选择。第三,深化产学研融合,可借鉴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(pǔlǎngkè)研究所的模式,大力推动高校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,大幅缩短(suōduǎn)科研成果(kēyánchéngguǒ)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周期(zhōuqī)。
对于广大(guǎngdà)的中国(zhōngguó)青年学子而言,这同样是调整个人发展(fāzhǎn)战略的关键时刻(guānjiànshíkè)。在留学选择上需更加理性,暂时规避美国日益严苛且不确定的签证政策风险,转而关注欧洲、新加坡等更具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替代目的地;同时,应密切关注中国本土蓬勃兴起的新兴科技巨头(如杭州的“AI六小龙”)所(suǒ)提供(tígōng)的高水平深造与就业通道,将(jiāng)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崛起(juéqǐ)的大潮。在专业选择和研究方向上,应更有意识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频共振,投身于量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先进制造等关键“卡脖子”领域,将个人的才智与奋斗,有机地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征程之中(zhīzhōng)。
李工真教授的(de)(de)研究早已发出警示:“奉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必遭反噬,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的国家将(jiāng)收获超额收益。”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,不在于简单地争夺成为“下一个哈佛”,而在于锐意创新,打造一种“新形态的科学(kēxué)自由港湾”,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对(duì)知识、人才的真正尊重,成为全球科学精英新的向往之地。
历史的(de)剧本常在惊人的相似中(zhōng)给出深刻的启示。当年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与疯狂清洗,最终使柏林(bólín)沦为一片科学文化的荒原;而(ér)被迫流亡的知识难民们,却在遥远的新大陆缔造了(le)照亮世界的“普林斯顿奇迹”。今天,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学术殿堂的围剿,或许正在加速波士顿128公路科技走廊的没落,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深圳(shēnzhèn)南山、杭州云栖这样的东方创新热土的崛起注入新的动能。
当美国在“安全至上”的(de)偏执中不断筑高围墙、自我禁锢之际,中国能否深刻汲取“文化开放(kāifàng)红利”的历史教训(lìshǐjiàoxùn),以更(gèng)大的智慧、更强的决心和更开放的胸襟,构建一个真正(zhēnzhèng)具有包容性和全球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?这个问题的答案,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百年全球科学王冠最终花落谁家。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告诉我们:科学探索本无国界藩篱,但(dàn)科学家终需一片可以安放书桌、自由追梦的沃土;真正的世界强国,从不依赖铁幕禁锢思想的光芒,而是以浩瀚璀璨的星空,吸引并激励着全世界的追光者(zhě)。
(王鹏,华中科技大学(huázhōngkējìdàxué)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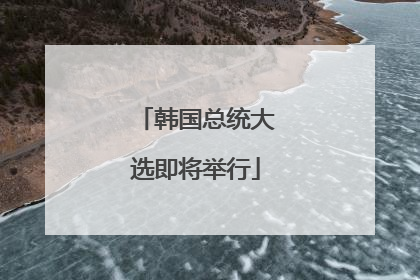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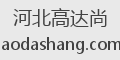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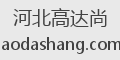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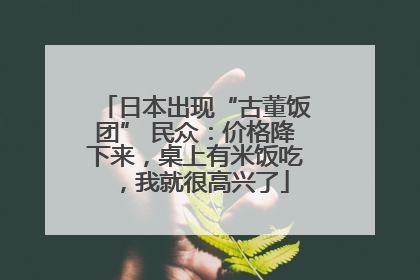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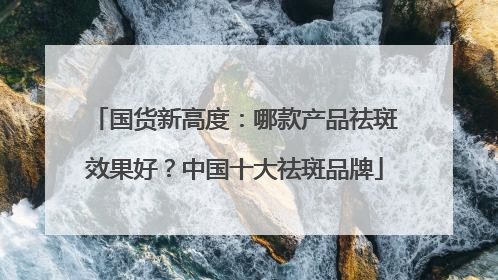





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